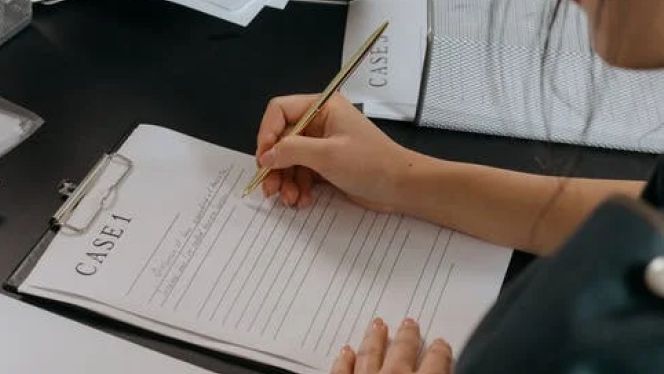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
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潇湘去?【注释】:
①津渡:渡口。
②可堪:那堪。
③驿寄梅花:引用陆凯寄赠范晔的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作者以远离故乡的范晔自比。
④郴(chén):郴州,今湖南郴县。
⑤幸自:本身。
【评解】
这首词是作者因坐党籍连遭贬谪时所写,表达了失意人的凄苦和哀怨的心情,流露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上片写旅途中所见景色,景中见情。下片抒发诗人内心的苦闷和愁恨心情。词意委婉含蓄,寓有作者身世之感。
【集评】
王国维《人间词话》: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此首写羁旅,哀怨欲绝。起写旅途景色,已有归路茫茫之感。末引“郴江”、“郴山”,以喻人之分别,无理已极,沉痛已极,宜东坡爱之不忍释也。
王方俊《唐宋词赏析》:这首词层次极为分明。开头两句都以对句起,都是平叙;中间第三句一顿;末两句是中心所在。虽是小词,用的是慢词作法。
--此词为作者绍圣四年(1097)贬谪郴州时在旅店所写。词中抒写了作者流徙僻远之地的凄苦失望之情和思念家乡的怅惘之情。词的上片以写景为主,描写了词人谪居郴州登高怅望时的所见和谪居的环境,但景中有情,表现了他苦闷迷惘、孤独寂寞的情怀。下片以抒情为主,写他谪居生活中的无限哀愁,他偶尔也情中带景。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写夜雾笼罩一切的凄凄迷迷的世界:楼台在茫茫大雾中消失;渡口被朦胧的月色所隐没;那当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更是云遮雾障,无处可寻了。当然,这是作者意想中的景象,因为紧接着的两句是“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词人闭居孤馆,只有在想象中才能看得到“津渡”。而从时间上来看,上句写的是雾濛濛的月夜,下句时间又倒退到残阳如血的黄昏时刻。由此可见,这两句是实写诗人不堪客馆寂寞,而头三句则是虚构之景了。这里词人运用因情造景的手法,景为情而设,意味深长。“楼台”,令人联想到的是一种巍峨美好的形象,而如今被漫天的雾吞噬了;“津渡”,可以使人产生指引道路、走出困境的联想,而如今在朦胧夜色中迷失不见了;“桃源”,令人联想到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一片乐土,而如今在人间再也找不到了。开头三句,分别下了“失”、“迷”、“无”三个否定词,接连写出三种曾经存在过或在人们的想象中存在过的事物的消失,表现了一个屡遭贬谪的失意者的怅惘之情和对前途的渺茫之感。
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两句则开始正面实写词人羁旅郴州客馆不胜其悲的现实生活。一个“馆”字,已暗示羁旅之愁。说“孤馆”则进一步点明客舍的寂寞和客子的孤单。而这座“孤馆”又紧紧封闭于春寒之中,置身其间的词人其心情之凄苦就可想而知了。此时此刻,又传来杜鹃的阵阵悲鸣;那惨淡的夕阳正徐徐西下,这景象益发逗引起词人无穷的愁绪。杜鹃鸣声,是古典诗词中常用的表游子归思的意象。以少游一个羁旅之身,所居住的是寂寞孤馆,所感受的是料峭春寒,所听到的是杜鹃啼血,所见到的是日暮斜阳,此情此境,只能以“可堪”道之。
“可堪”者,岂堪也,词人在这重重凄厉的气围中,又怎能忍受得了呢?王国维评价这两句词说:“少游词境最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
过片“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连用两则友人投寄书信的典故,极写思乡怀旧之情。“驿寄梅花”,见于《荆州记》记载;“鱼传尺素”,是用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诗意,意指书信往来。少游是贬谪之人,北归无望,亲友们的来书和馈赠,实际上并不能给他带来丝毫慰藉,而只能徒然增加他别恨离愁而已。
因此,书信和馈赠越多,离恨也积得越多,无数“梅花”和“尺素”,仿佛堆砌成了“无重数”的恨。词人这种感受是很深切的,而这种感受又很难表现,故词人手法创新,只说“砌成此恨无重数”。有这一“砌”字,那一封封书信,一束束梅花,便仿佛成了一块块砖石,层层垒起,以至于达到“无重数”的极限。这种写法,不仅把抽象的微妙的感情形象化,而且也可使人想象词人心中的积恨也如砖石垒成,沉重坚实而又无法消解。
在如此深重难排的苦恨中,迸发出最后二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从表面上看,这两句似乎是即景抒情,写词人纵目郴江,抒发远望怀乡之思。郴江,发源于湖南省郴县黄岭山,即词中所写的“郴山”。郴江出山后,向北流入耒水,又北经耒阳县,至衡阳而东流入潇水湘江。但实际上,一经词人点化,那山山水水都仿佛活了,具有了人的思想感情。这两句由于分别加入了“幸自”和“为谁”两个字,无情的山水似乎也能听懂人语,词人在痴痴问询郴江:你本来生活在自己的故土,和郴山欢聚在一起,究竟为了谁而竟自离乡背井,“流下潇湘去”呢?
实际上是词人面对着郴江自怨自艾,慨叹自己好端端一个读书人,本想出来为朝廷做一番事业,怎知到如今竟被卷入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呢?词人笔下的郴江之水,已经注入了作者对自己离乡远谪的深长怨恨,富有象征性,故而这结尾两句的意蕴就更深长丰富了。
此词表达了失意者的凄苦和哀怨的心情,流露了对现实政治一定程度的不满。在写作上,词人善用对句写景抒情。上片开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雾霭与月色对举,造成一种朦胧的意境,笼罩全词;下片开头亦用对句,“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虽然表现的都是朋友的信息和寄赠这同一内容,却能造成书信往来频频不断的气势,与“砌成此恨无重数”相照应。
总之,此词以新颖细腻、委婉含蓄的手法描写了作者在特点环境中的特定心绪,抒发了内心不能直言的深曲幽微的贬徒之悲,寄托了深沉哀婉的身世之感,使用写实、象征的手法营造凄迷幽怨、含蓄深厚的词境,充分体现了作者身为北宋婉约派大家的卓越艺术才能。
zb258.com精选阅读
踏莎行·小径红稀 [宋] 晏殊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此词描绘暮春景色,上片写郊外景,下片写院内景,最后以“斜阳却照深深院”作结,流露出淡淡的哀愁。起首三句描绘一幅具有典型特征的芳郊春暮图:小路两旁,花儿已经稀疏,只间或看到星星点点的几瓣残红;放眼一望只见绿色已经漫山遍野;高台附近,树木繁茂成荫,一片幽深。“红稀”“绿遍”“树色阴阴”,标志着春天已经消逝,暮春气息很浓。三句所写虽系眼前静景,但“稀”“遍”“见”这几个词却显示了事物发展的进程和动态。从“小径”“芳郊”“高台”的顺序看,也有移步换形之感。“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所写的杨花扑面,也是暮春典型景色。但词人描绘这一景象时,却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写成春风不懂得约束杨花,以致让它漫天飞舞,乱扑行人之面。这一方面暗示已经无计留春,只好听任杨花飘舞送春归去;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杨花的无拘无束和活跃的生命力。这里虽写暮春景色,却无衰颓情调,富有生趣。“蒙蒙”“乱扑”,极富动态感。“行人”二字,点醒以上所写,都是词人郊行所见。过片“翠叶藏莺,珠帘隔燕”两句,分写室外与室内,一承上,一启下,转接自然。上句说翠绿的树叶已经长得很茂密,藏得住黄莺的身影,与上片“树色阴阴”相应;下句说燕子为朱帘所隔,不得进入室内,引出下面对室内景象的描写。着“藏”“隔”二字,生动地写出了初夏嘉树繁阴之景与永昼闲静之状。“炉香静逐游丝转”写如此闲静的室内,香炉里的香烟,袅袅上升,和飘荡的游丝纠结、缭绕,逐渐融合一起,分不清孰为香烟,孰为游丝了。“逐”“转”二字,表面上是写动态,实际上却反托出整个室内的寂静。“逐”上着一“静”字,境界顿出。结拍“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跳开一笔,写到日暮酒醒梦觉之时,原来词人午间小饮,酒困入睡,等到一觉醒来,已是日暮时分,西斜的夕阳正照着这深深的朱门院落。这里点明“愁梦”,说明梦境与春愁有关。梦醒后斜阳仍照深院,遂生初夏日长难以消遣之意。贺铸《薄幸》词“人间昼永无聊赖。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也正是此意。
芳心苦/踏莎行 [宋] 贺铸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语。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注释】
①回塘:环曲的水塘。
②别浦:水流的叉口。
③红衣:此指红荷花瓣。
④芳心:莲心。
⑤返照:夕阳的回光。
⑥骚人:诗人。
⑦“当年”句:韩偓《寄恨》诗云:“莲花不肯嫁春风。”
【评解】
此词咏秋荷,于红衣脱尽,芳心含苦时,迎潮带雨,依依人语,自有一种幽情盘结其间,令人魂断。前人谓贺铸“戏为长短句,皆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以此词观之,可谓知言。
【集评】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骚情雅意,哀怨无端。
沈祖棻《宋词赏析》:这首词是咏荷花的,暗中以荷花自比。诗人咏物很少止于描写物态,多半有所寄托。因为在生活中,有许多事物可以类比,情感可以相通,人们可以利用联想,由此及彼,发抒文外之意。
《宋史·文苑传》载贺铸“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少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竟以尚气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
--此词全篇咏写荷花,借物言情。词中以荷花自况,以荷花的清亮绝俗不免凋零清苦,寄托个人身世的感喟,抒写怀才不遇的苦闷。
上片起首两句两句互文同指,先画出一个绿柳环绕、鸳鸯游憩的池塘,见荷花所处环境的优美。水上鸳鸯,双栖双宿,常作为男女爱情的象征,则又与水中荷花的幽独适成对照,对于表现它的命运是一种反衬。回塘,意即曲折回环的池塘;别浦,即江河支流的水口。
第三句“绿萍涨断莲舟路”意谓因水面不甚宽广,池塘中很容易长满绿色的浮萍,连采莲小舟来往的路也被遮断了。莲舟路断,则荷花只能在回塘中自开自落,无人欣赏与采摘。句中“涨”定“断”字,都用得真切形象,显现出池塘中绿萍四合、不见水面的情景。
四五两句写荷花寂寞地开落、无人欣赏。断无,即绝无。不但莲舟路断,无人采摘,甚至连蜂蝶也不接近,“无蜂蝶”也包含了并无过往游人,荷花只能在寂寞中逐渐褪尽红色的花瓣,最后剩下莲子中心的苦味。这里俨然将荷花比作亭亭玉立的美人,“红衣”、“芳心”,都明显带有拟人化的性质。“幽香”形容它的高洁,而“红衣脱尽芳心苦”则显示了她的寂寞处境和芳华零落的悲苦心情。这两句是全词的着力之笔,也是将咏物、拟人、托寓结合得天衣无缝的化工之笔。既切合荷花的形态和开花结实过程,又非常自然地绾合了人的处境命运。此二句形神兼备,虚实结合,将词人内心的情感表达得极为动人。
过片两句,描绘夏秋之际傍晚雨后初睛的荷塘景色,形象地烘托了“红衣脱尽”的荷花黯淡苦闷的心境。夕阳的余辉,照映在浦口的水波上,闪耀着粼粼波光,像是在迎接晚潮;流动的云彩,似乎还带着雨意,偶而有几滴溅落在荷塘上。
接下来一句,写荷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看上去似乎在满怀感情地向骚人雅士诉说自己的遭遇与心境。这仍然是将荷花暗比作美人。着一“似”字,不但说明这是词人的主观感觉,且将咏物与拟人打成一片,显得非常自然。这一句是从屈原《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引伸、生发而成,“骚人”指屈原,推而广之,可指一切怜爱荷花的诗人墨客。
说荷花“似与骚人语”,曲尽它的情态风神,显示了它的幽洁高雅。蜂蝶虽不慕其幽香,骚人却可听它诉说情怀,可见它毕竟还是不乏知音。
结尾两句,巧妙地将荷花开放与凋谢的时节与它的生性品质、命运遭际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表现出美人、君子不愿趋时媚俗的品质和严肃不苟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他们年华虚度,怀才不遇的悲哀。嫁春风,语本李贺《南园》:“嫁与东风不用媒。”而韩偓《寄恨》“莲花不肯嫁春风”句则为贺词直接所本。桃杏一类的花,竞相在春天开放,而荷花却独在夏日盛开,“不肯嫁春风”,正显示出它那不愿趋时附俗的幽洁贞静个性。然而秋风一起,红衣落尽,芳华消逝,故说“被秋风误”。“无端”与“却”,含有始料所未及的意蕴。这里,有对“秋风”的埋怨,也有自怨自怜的感情,而言外又隐含为命运所播弄的嗟叹,可谓恨、悔、怨、嗟,一时交并,感情内涵非常丰富。
这两句同样是荷花、美人与词人三位而一体,咏物、拟人与自寓的完美结合。
作者在词中隐然将荷花比作一位幽洁贞静、身世飘零的女子,借以抒发才士沦落不遇的感慨。《宋史·文苑传》载贺氏“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
虽要权倾一时,少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竟以尚气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这些记载,对于理解此词的深意颇有帮助。
踏莎行·自沔东来 [宋] 姜夔
自沔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
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
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
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
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注释】:
燕燕、莺莺:指所爱之人。苏轼赠张先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
华胥:梦境。《列子》,“黄帝昼寐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
淮南:指合肥,作者有情人在合肥,但他从汉阳去金陵,未能在中途去探望。
白石二十多岁时,在合肥有过一段情缘,后来分手了,但白石对旧日情人始终恋恋不忘,这成为他心灵深处永远的悲哀和伤痛。所谓时间能冲淡一切的说法并不适用于至情至性之人,余于白石尤然。从此词看,白石所恋似是姊妹二人,句中出现“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可证。其他词中也出现过“大乔小乔”,“桃根桃叶”二人连用的典故,亦可为证。淳熙十四年(1187丁未)元旦,姜夔从第二故乡汉阳(宋时沔州)东去湖州途中抵金陵时,梦见了往日的情人,写下此词。
上片写梦,哀怨之极。北宋时苏轼听说张先老人时已八十五岁买妾,作诗调侃道:“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这首词一开始即借“莺莺燕燕”字面称往日的情人,从称呼中流露出一种卿卿我我的缠绵情意。这里还有第二重含义,即比喻其人体态“轻盈”如燕,声音“娇软”如莺。这“燕燕轻盈,莺莺娇软”本以为是现实中的旖旎风光,读下句方知乃是词人梦中所见的情境。《列子·黄帝》载“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故词写好梦云“分明又向华胥见”。夜有所梦,乃是日有所思的缘故。以下又通过梦中情人的自述,体贴对方的相思之情。她含情脉脉道:在这迢迢春夜中,“薄情”人(此为昵称)啊,你知道我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吗?言下大有“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的意味。“染”字用得精妙,惟辛弃疾《鹧鸪天》“春风不染白髭须”可比。
过片写别后睹物思人,旧情难忘。“别后书辞”,是指情人寄来的书信,检阅犹新;“别时针线”,是指情人为自己所做衣服,仍有遗香。二句虽仅写出物件,而不直接言情,然读来皆情至之语这是托物言情的妙处。紧接着承上片梦见事,进一层写伊人之情。“离魂暗逐郎行远”,“郎行”即“郎边”,当时熟语,说她甚至连魂魄也脱离躯体,追逐我来到远方。比之韦应《木兰花》“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更多一层深情。然而魂魄飞越千山万水,寻觅情郎的结果却是“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末二句写作者梦醒后深情想象情人魂魄归去的情景:在一片明月光下,淮南千山是如此清冷,她就这样独自归去无人照管。一种惜玉怜香之情,一种深切的惭愧负疚之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
这首词紧扣感梦之主题,以梦见情人开端,又以情人梦魂归去收尾,意象浑成,境界空灵清远。词的后半部分,尤见幽邃清冷。在构思上借鉴了唐传奇《离魂记》,记中倩娘居然能以出窍之灵魂追逐所爱者远游,着想奇妙。在意境与措语上,则又融合了杜诗《梦李白》“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咏怀古迹》“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句意。妙在自然天成,不著痕迹。王国维说:“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人间词话》删稿)可见评价之高。白石的情词不惟写自己的相思寂寞之苦,而且照应双方,多从对方着眼,为对方设身处地地着想,亦可见白石之至情至性。
踏莎行·候馆梅残 [宋] 欧阳修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这是一首写离情的佳作。在抒写游子思乡的同时,联想到闺中人相忆念的情景,写出了两地相思之情。上片写马上征人。以景为主,融情于景;下片写闺中思妇。以抒情为主,情寓景中。构成了清丽缠绵的意境。这首词表现出欧词深婉的风格,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一首。这首词是欧阳修词的代表作之一。在婉约派词人抒写离情的小令中,这是一首情深意远、柔婉优美的代表性作品。上片写离家远行的人在旅途中的所见所感。开头三句是一幅洋溢着春天气息的溪山行旅图:旅舍旁的梅花已经开过了,只剩下几朵残英,溪桥边的柳树刚抽出细嫩的枝叶。暖风吹送着春草的芳香,远行的人就这美好的环境中摇动马缰,赶马行路。梅残、柳细、草薰、风暖,暗示时令正当仲春。这正是最易使人动情的季节。从“摇征辔”的“摇”字中可以想象行人骑着马儿顾盼徐行的情景。融怡明媚的春光,既让人流连欣赏,却又容易触动离愁。开头三句以实景暗示、烘托离别,而三、四两句则由丽景转入对离情的描写:“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因为所别者是自己深爱的人,所以这离愁便随着分别时间之久、相隔路程之长越积越多,就像眼前这伴着自己的一溪春水一样,来路无穷,去程不尽。此二句即景设喻,即物生情,以水喻愁,写得自然贴切而又柔美含蓄。下片写闺中少妇对陌上游子的深切思念。“寸寸柔肠,盈盈粉泪。”过片两对句,由陌上行人转笔写楼头思妇。“柔肠”而说“寸寸”,“粉泪”而说“盈盈”,显示出女子思绪的缠绵深切。从“迢迢春水”到“寸寸肠”、“盈盈泪”,其间又有一种自然的联系。接下来一句“楼高莫近危阑倚”,是行人心里对泪眼盈盈的闺中人深情的体贴和嘱咐,也是思妇既希望登高眺望游子踪影又明知徒然的内心挣扎。最后两句写少妇的凝望和想象,是游子想象闺中人凭高望远而不见所思之人的情景:展现楼前的,是一片杂草繁茂的原野,原野的尽头是隐隐春山,所思念的行人,更远春山之外,渺不可寻。这两句不但写出了楼头思妇凝目远望、神驰天外的情景,而且透出了她的一往情深,正越过春山的阻隔,一直伴随着渐行渐远的征人飞向天涯。行者不仅想象到居者登高怀远,而且深入到对方的心灵对自己的追踪。如此写来,情意深长而又哀婉欲绝。单从艺术特色上分析,此词主要运用了以下四种艺术手法。以乐写愁,托物兴怀。这种手法运用得很巧妙。词的上片展现了一位孤独行人骑马离开候馆的镜头。在这画面里,残梅、细柳和薰草等春天里的典型景物点缀着候馆、溪桥和征途,表现了南方初春融和的气氛。这首词以春景写行旅,以乐景写离愁,从而得到烦恼倍增的效果。寓虚,富于联想,也是这首词的一个艺术特点。梅、柳、草,实景虚用,虚实结合,不仅表现了春天的美好景色,而且寄寓了行人的离情别绪。作者从各个角度表现离愁,的确非常耐人寻味,有无穷的韵外之致。化虚为实,巧于设喻,同样是此篇重要的艺术手段。“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便是这种写法。“愁”是一种无形无影的感情。“虚”的离愁,化为“实”的春水;无可感的情绪,化为可感的形象,因而大大加强了艺术效果。逐层深化,委曲尽情,更是这首词显著的艺术特色。整个下片,采用了不同类型的“更进一层”的艺术手法,那深沉的离愁,便被宛转细腻地表现出来了,感人动情。整首词只有五十八个字,但由于巧妙地运用了以乐写愁、实中寓虚、化虚为实、更进一层等艺术手法,便把离愁表现得淋漓尽致,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所以成了人们乐于传诵的名篇。
行香子·树绕村庄 [宋] 秦观
树绕村庄,
水满陂塘。
倚东风、豪兴徜徉。
小园几许,
收尽春光。
有桃花红,李花白,
菜花黄。
远远围墙,
隐隐茅堂。
飏青旗、流水桥旁。
偶然乘兴,
步过东冈。
正莺儿啼,
燕儿舞,蝶儿忙。【注释】:
此词以朴实、生动、清新、通俗的语言和明快的节奏、轻松的情致,极富动感地描绘了作者乘兴徜徉所见的朴质、自然的村野田园风光,达的词的节奏和词人的情感之间和谐的统一。
上片以“小园”为中心,写词人所见的烂漫春光。开头两句,先从整个村庄着笔:层层绿树,环绕着村庄;一泓绿水,涨满了陂塘。这正是春天来到农家的标志,也是词人行近村庄的第一印象。接下来“倚东风、豪兴徜徉。”两句,出现游春的主人公。“东风”点时令,“豪兴”说明游兴正浓,“徜徉”则显示词人只是信步闲游,并没有固定的目标与路线。这两句写出词人怡然自得的神态。“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在信步徜徉的过程中,词人的目光忽然被眼前一所色彩缤纷、春意盎然的小园所吸引,不知不觉停住了脚步:这里有红艳的桃花,雪白的李花,金黄的菜花。色彩鲜明,香味浓郁,只用清新明快的几个短语道出,偏写尽了无限春光。
下片移步换形,从眼前的小园转向远处的茅堂小桥。远处是一带逶迤缭绕的围墙,墙内隐现出茅草覆顶的小屋,在小桥流水近旁,飘扬着乡村小酒店的青旗。这几句不但动静相间,风光如画,而且那隐现的茅堂和掩映的青旗又因其本身的富于含蕴而引起游人的遐想,自具一种吸引人的魅力。“偶然乘兴,步过东冈。”这两句叙事,插在前后的写景句子中间,使文情稍作顿挫,别具一种萧散自得的意趣。“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这是步过东边的小山冈以后展现在眼前的另一派春光。和上片结尾写不同色彩的花儿不同,这三句写的是春天最活跃的三种虫鸟,以集中表现春的生命活力。词人用“啼”、“舞”、“忙”三个字准确地概括了三种虫鸟的特性,与上片结尾对映,进一步强化了生机无限的春光。
在唐、五代和北宋的词苑中,描绘农村田园风物的词并不多见。从这一意义上说,秦观的这首《行香子》,在词境的开拓方面,起了比较大的作用,堪与苏轼的五首《浣溪沙》相提并论。在秦观的作品中,格调如此轻松、欢快的作品也是不多见的。